至于原因,司法部表示,科济列夫散布了有关俄罗斯联邦的虚假信息,并给俄罗斯武装部队树立了负面形象。再加上科济列夫不断与外国政府互动,久居国外。所以如今被定义为“外国特工”,不算冤枉。

(俄外长拉夫罗夫)
这名科济列夫,算是俄罗斯首任外长了。从苏联时期开始就在外交部工作,并且亲眼见证了苏联的解体。苏联解体后,其成为了俄罗斯第一任外长,并试图推动俄罗斯“全盘倒向美西方”。
科济列夫的外交理念是这样的,他认为俄罗斯应该放弃传统地缘政治思维,以“普世价值观”取代国家利益。在1992年的联合国演讲中,他就曾宣称“俄罗斯没有国家利益”,并强调“俄罗斯属于西方文明圈”,这种自我矮化的战略思维,直接导致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美国。
在外交实践中,他同样采取了战略退让的策略。科济列夫时期,俄罗斯仓促地从波罗的海三国和东德撤军,导致北约防线推进到俄罗斯边境,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带。同时,其主动放弃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,间接引发车臣战争,削弱了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的控制。
在海湾战争中,科济列夫也支持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,并默认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,甚至未争取俄罗斯在中东的传统利益。这种“逢美必合”的姿态,当时还被西方媒体戏谑为是“是部长”,也就是对美国永远都习惯性说“是”的部长。
在经济领域,其推动的所谓“休克疗法”和经济自由化,也是试图通过西方援助实现转型,但最终导致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。
俄方消息显示,科济列夫早在2012年的时候,就迁居到美国居住了,现在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“反俄先锋”。在俄乌冲突爆发后,其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,他呼吁俄罗斯外交官辞职,劝他们叛国转向美国。近日,他甚至公开喊话泽连斯基,希望泽连斯基能和西方要到更多的武器,不要对俄方做出任何让步。
也正是这件事情再次引起了俄罗斯民众的公愤,司法部才最终出手,给其安上了“外国特工”的名号。

(俄罗斯首任外长科济列夫(右))
“前辈”外长落了个这下场,现任俄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就迅速针对美俄关系,进行了一番表态。
拉夫罗夫表示,现在美俄正在进行谈判,在这个过程中,俄方非常清楚什么对于俄罗斯来说才是“真正互利”的协议,所以未来俄罗斯会吸取教训,不再允许协议中出现任何会使俄方在经济或是其他领域,对他国产生依赖的条款。
放在当前的背景下,拉夫罗夫的这一表态,既有为俄罗斯发声的意义,同时也有为自己澄清的意味。即不管什么时候,俄方都会谨记亲美带来的教训,避免让俄罗斯跳入同一个陷阱。
从2004年接任外长到现在,拉夫罗夫任职已有20多年,从其这么多年来的表现也可以明显看出,其在外交理念上和科济列夫存在明显的不同。
拉夫罗夫主导的外交政策以维护俄罗斯主权和安全为核心,明确反对单极世界,主张构建多极化国际秩序。在这一理念引导下,他多次批评德国盲目追随美国政策导致自身利益受损,同时高度评价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。
俄乌冲突爆发后,他坚决反对北约东扩,支持克里米亚公投入俄,并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,宣称要以法律协议保障俄罗斯安全;叙利亚问题上,他主张联合伊朗、土耳其构建 “阿斯塔纳进程”,反对西方推翻巴沙尔政权。
在外交语言风格上,他更是多次以“西方的虚伪”“双重标准”等词抨击美欧,甚至将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比作“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”。
总之,其做法和理念同科济列夫截然不同。

(科济列夫)
最后,作为两任外长,科济列夫与拉夫罗夫的差异,本质上其实也是俄罗斯国家身份认知的代际冲突。
科济列夫这边,误判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,认为俄罗斯可通过“文明皈依”获得西方接纳。这种幻想导致其在北约东扩、经济转型等问题上一退再退,最终成为西方“民主改造”的牺牲品。
而拉夫罗夫,则亲眼目睹了西方对俄罗斯的持续挤压,深刻意识到“融入西方”就是伪命题。因此,他将外交重心转向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,通过“主权、安全、发展”三位一体的逻辑重构国际秩序。
总之,科济列夫的亲美路线是俄罗斯转型期的特殊产物,其失败证明以妥协求安全必然丧失安全;拉夫罗夫的强硬外交则标志着俄罗斯从“战略幼稚”走向“战略觉醒”,尽管代价高昂,但为国家生存赢得了空间。
两人的对比,不仅是个人外交风格的差异,更是两种世界观的碰撞,前者相信所谓“普世价值”的救赎,后者坚持“强权政治”的现实。未来这种碰撞还将继续塑造俄罗斯的国际角色,也将深刻影响21世纪的大国博弈格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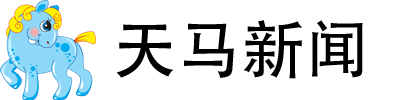
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





